鲁哀公曾这么问有若:“年饥,用不足,如之何?”有若的答案是减税。纵使轻敛薄赋是古来政治家的理想,在非常时期之间,却也往往不得不加敛于民,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间永远无法磨合之处。
唐代财政政策“总无名之暴赋”
在面对政权危机的当下,也大多选择支持某种程度的增税。如何在暴敛与轻赋间取得一完美平衡,如同走钢索般惊险而不坠于地,则是一个为政的艺术,稍不小心,则陷入了“总无名之暴赋”的陷阱中,成了连盗臣也不如的聚敛之臣。
 鲁哀公
鲁哀公中唐以来版籍帐册早已失实,面对动乱之下,陆贽也不得不承认加赋乃一权衡清楚下的决策。如何取的巧,取的刚好,取的让人民心服口服,便是一个执政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陆贽盛赞租庸调法名目清楚,“有田则有租,有身则有庸,有家则有调”,虽然颇为复杂,但条列的清楚明白,纵有加税,亦有其名目。
 租庸调
租庸调在这个部分,他虽然从未表明,但其所长和所处之立场,与刘晏大致是相同的,其重点在于以租庸调为原则,在不加税的前提之下,整合分配资源。这个理财方式或许颇有大用,却也往往有着繁复的缺失,无形在过程中充满了人治的色彩。
 安史之乱
安史之乱纵使如此,各种额外的负担仍旧不断的增加,这也是安史之乱开始至两税法实施之间一个不得不的趋势,这出自于朝廷所需要的开销日渐增加。在正税之外,便出现了各种加征的名目,或许稍微填补了国库的空洞,实际上却也苦了人民。
 唐代窖藏金银
唐代窖藏金银“量出制入”的税收制订原则
对于农民而言,他们痛苦的来源除了税额的增加,更多是来自于日趋复杂的各种杂征,“旬输月送”实在让他们不堪其扰。为了让人民有着更加简便的赋税方式,才会有两税法的出现。因此两税法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,便在于其纳税方式的简便,在此成了“总无名之暴敛”的关键,重点在于赋出无名,又以此为长久之计。针对此点,陆贽甚至这么攻击:“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,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。”这只是两税法赋出无名的部分。
 陆贽
陆贽至于暴赋的部分,两税法下唐代农民的赋税支出,确实较租庸调时期高出不少,单是谷物的支出便由2.8石增加至5.16石,多出了将近一倍。两税时代不征收布帛而收钱,折算之后也有7.78贯,即7780文钱。
依据陆贽的记载,两税法初行时每匹布可折3200-3300文钱左右,在此以3250文钱计。租庸调法时代平均每户要缴纳2.5匹布帛,约值8250钱,虽比两税法时代多出了470文钱。再扣掉米价折算后,确实较租庸调法的时代略有增加,但还称不上是暴敛。经过了数十年,到了陆贽的时代,物价有所波动,布帛从原本3200-3300的水准降至1500-1600文钱之间,单是布帛的缴纳便凭空多出了一倍。到了这个时候,虽然朝廷无意暴敛,数十年间的转折却也够让农民生出这样的感受了。
陆贽本身是支持租庸调法的。他承认国家的动乱是时弊,却不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租庸调法。只要国家的状况恢复稳定,他是支持回复租庸调法的,或者依租庸调法的精神令创新制,绝非如同杨炎一般切断了与过去制度连结的再造百度。更重要的,是租庸调法除了征收税目清楚明白外,更是保留了先王建制以来的基本精神,即薄敛与为民治产。
很可惜的,陆贽多少回避了中唐以来租庸调法实施的问题,而租庸调法的顺利执行与否,与均田制是攸栖相关的。高宗以来已经渐渐无法管理永业田的买卖,玄宗朝励精图治,或许略有改善,实际上却也没有太大的变革。至少在出土的敦煌土地文书中,我们无法看到土地分配的问题有改善的趋势。如此渐行恶化,是一个社会发达下的结果,造成的便是如同杨炎所说:

纵使没有安史之乱,租庸调法早已只见于空文,而非确实执行的法令了。陆贽强调了安史之乱等内乱造成的时弊,却忽略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已然难以实施租庸调法的事实。况且从前面的讨论,我们知道租庸调法对于广占土地的人而言确实是薄敛,对于地狭田窄的一般农民而言却是相当的不利。均田制发展的结果,已然使的就有薄敛的精神荡然无存。
 古籍上的均田制插图
古籍上的均田制插图在国家财政的整体规划上,两税法与租庸调法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歧异,那便是赋税征收与国家预算支出的原则,由原有的量入为出,一举转变为量出制入。有关于“量出制入”的税收制订原则,虽早已存在朝廷的财政体制中,光明正大的提出来,杨炎倒是第一个人,这却也是两税法最受批评的原因之一。
若简单的从字面上理解,“量入为出”与“量出制入”两者间的确存在着明显的歧异,在此也却实有必要稍作探讨。
“量入为出”是儒家的财政思想,见《礼记王制》:

以三十年的平均收入决定国家的开支,这也考量到农民负担能力的水准,依据这样的方法,可以“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”,农民也不会有贫困的问题。有关今日农民税收的负担能力,纵使在统计方法普及且发达的今日,依旧无法清楚计算出其负担能力的上限。这毕竟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问题,各种因素皆会改变农民的赋税负担力。
 古代推税票
古代推税票在丰年时,农民的赋税能力自然较高,到了荒年时,纵使是粒米之征也会被视为无理的横征暴歛。这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思想中,却不是个核心议题,多数的政治家都继承了儒家的思想,以为“什一之税”便是最合理的税额。

十分之一的比例,当然不是一个精密计算后的结果,只是古代政治思想家依据其经验,大概摸索出来的上限数额。就制度上来看,历代的政权也奉行这样的理想,努力将税收的数目压低至百分之十以下,甚至远低于该数额。一方面强调了本身的德政,也加强了其政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。另一方面,以农民的税额负担力为基础进行征收的计算,也隐含了古来以民为尚的施政理念。
参考文献:
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《陆贽集》《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》《唐代经济思想研究》《礼记译解》《唐代财政史稿》《通典》
《中国古代籍帐研究》
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634936527627737648&wfr=spider&for=pc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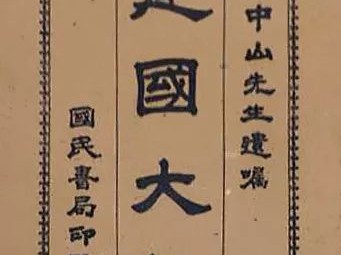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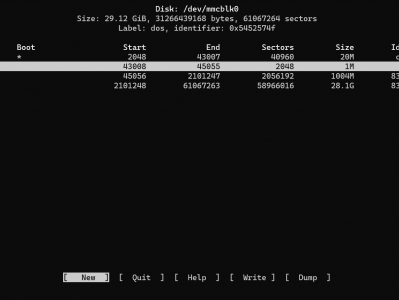






0 留言